在一架满载商务人士的飞机上,鲍勃 (Bob)一边在笔记本电脑上阅读《华尔街日报》,一边下载资料,同时还忙着整理飞抵纽约后要在第一场会议上演示的PPT文档。他不禁陶醉于自己工作计划、待办清单及电话簿的井井有条。这时,鲍勃偶然瞥见隔壁排的一位女士,正将一些便签夹入备忘录中……不是吧?她怎么好像是从远古时代穿越来的?嗨,夫人,醒醒吧!嗅一嗅电脑时代的气息吧!现在,鲍勃已走出机场,和几十位旅客一起不耐烦地等着出租车。终于轮到他了,可还没摸到车门把手,一个彪形大汉突然闯到他身前,几乎将他撞翻。公事包飞到一边,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散落在人行道上。当鲍勃愤愤地收拾着这些高科技产品时,忽然发现备忘录的主人,也就是那位女士,款款地迈入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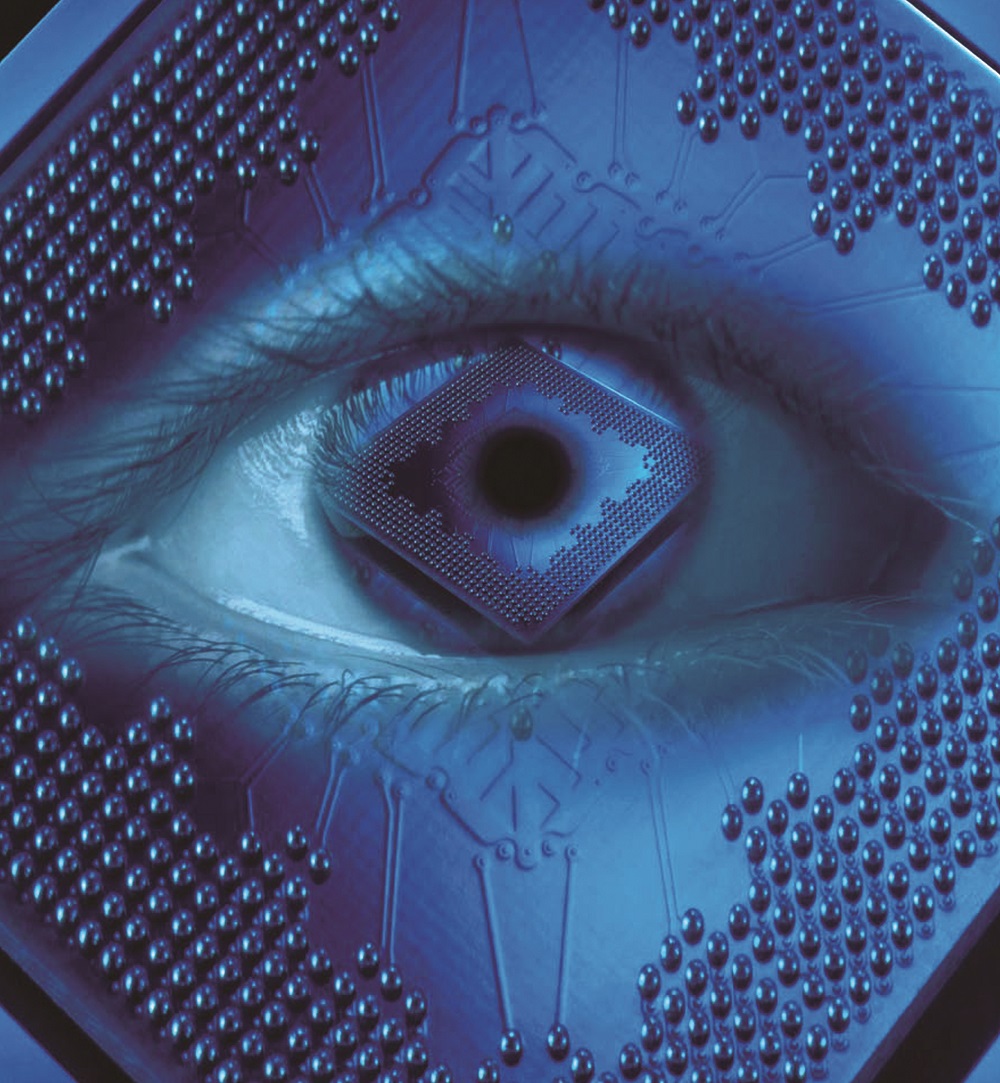
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交流方式,也迅速而深远地改变着我们的大脑。日常使用的高科技产品——电脑、智能电话、视频游戏、谷歌和雅虎等搜索引擎,刺激着脑细胞的改变和神经递质的释放。它们在逐渐弱化大脑旧有神经通路的同时,也强化形成了新的神经通路。科技革命使我们的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
数字科技不仅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还改变着我们的感觉和行为。人们通过互联网和数字科技进行娱乐、讨论政见、与友人同事交流。当不断进化的大脑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新科技的使用技巧时,一些最基本的社交能力(比如在交谈中察言观色,或通过细微的动作捕捉情感蕴意等)却被慢慢弱化。200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每在电脑前度过一小时,与他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就会减少约30分钟。
“数字土著”
如今的年轻人被冠以“数字土著”的称号。对他们而言,没有电脑、没有全天播放的电视新闻、没有互联网或没有手机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数字土著很少去图书馆,更别说用传统的百科全书来查询信息了——谷歌、雅虎及其他在线搜索引擎才是他们的新宠。“数字土著”的大脑神经网络已经显著区别于“数字移民”。所谓“数字移民”,指的是数字/电脑时代来临时已经长大成年的人,包括婴儿潮时代出生的大多数人。他们大脑的基本回路是在直接交往为主要社交方式的时期形成的。

我们的大脑每天长时间浸泡在高科技中,就连婴儿和儿童也不例外。2007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1,000多名儿童一天的正常活动。结果显示:75%的孩子每天都要看电视,32%看录像或DVD。此类活动平均每天耗时1小时20分钟。在这些孩子当中,五六岁的儿童平均每天还要花费50分钟使用计算机。恺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8~18岁年轻人的大脑平均每天有8个半小时在接受数字或视频信号的刺激。该研究报告称,人们接触大多数科技都是被动的,比如看电视和视频 (每天4小时) 或者听音乐(每天1小时45分钟);不过,接触有些科技则是主动的,需要用心去参与,比如玩电子游戏(每天50分钟)或使用计算机(每天1小时)。
众所周知,大脑的神经回路每时每刻都会对输入的信号作出反应。人们每天花大量时间去网上冲浪、收发电邮、参加视频会议、进行即时通讯以及网上购物,这些数字信号不断刺激着我们的大脑神经。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研究,想要弄清楚下列问题:长时间使用电脑会对大脑的神经回路产生多大影响?建立一个新的大脑回路到底有多快?我们能否观察并测量已经发生的改变?
搜索大脑
本文作者之一斯莫尔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心理学及神经影像学专家苏珊·布克哈默(Susan Bookheimer)和蒂娜·穆迪(Teena Moody)的帮助。我们计划让受试者在联网计算机上完成一项常见任务——利用谷歌来检索精确信息,同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观察他们大脑的活动情况。

颇费一番周折之后,我们终于招募到了3位从未使用过个人计算机的自愿者。这些五六十岁的受试者对数字科技十分生疏,但他们愿意尝试。为了比较受试者的大脑活动情况,我们还征集了3位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状况都与前者相似、但熟知电脑操作的自愿者。实验中,我们要求受试者利用谷歌针对不同主题搜索特定且精确的信息,比如食用巧克力对健康有什么益处,筹划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旅游等等。
接下来,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受试者使用互联网时,用fMRI扫描他们的大脑——因为实验时受试者必须身处fMRI狭长的测试台上,那里没有空间放置电脑、鼠标及键盘。为了让受试者在fMRI里也能进行谷歌搜索,我们为他们佩戴了一副可以显示网页图像的护目镜,并在某一合适的位置放一个小型键盘。受试者可以操控“模拟”计算机的屏幕,并用一根手指触碰小键盘进行选择和搜索。
要确保fMRI能够测量大脑中控制互联网搜索的神经回路,需要剔除其他的刺激因素。为此,我们添加了一项对照任务——在fMRI扫描期间,受试者透过护目镜阅读几页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fMRI扫描结果中剔除掉因阅读文本、观看图像或集中精力而产生的非特异大脑活动。

我们只希望观察并测量由网络搜索引起的大脑活动,比如寻找目标关键词、从数个选项中迅速作出选择,以及当某个特定的搜索结果无用时返回上一页面等。实验中,简单的阅读文本任务和互联网搜索任务交替进行。另外我们还严格控制了由网页上常见的照片和图像引起的非特异大脑刺激活动。
为了确定能否训练互联网新手的大脑,我们在第一次大脑扫描之后,要求每个受试者每天花1小时进行网上搜索,并持续5天。我们对熟悉电脑操作的对照受试者提出了同样要求。历经5天的搜索训练后,所有受试者将再次接受fMRI扫描。
大脑的改变
正如我们此前预测的那样,阅读文本时,受试的电脑新手和电脑老手的大脑并未显示有何不同。两组受试者对这项脑力任务都有多年经验,因而他们的大脑对阅读书籍颇为熟悉。相比之下,在谷歌上搜索时,两组受试者则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神经活动谱。基线扫描显示,电脑老手大脑左半球一处被称为背外侧额叶前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的特殊神经网络被激活;而电脑新手的这一脑区被激活的迹象则微乎其微。
在设计这套实验时,我们曾担心5天的时间可能不足以观察到变化的发生。但是经过5天的练习之后,电脑新手大脑中的背外侧额叶前皮质处相同的神经回路变得活跃起来。仅仅5个小时的网上生活就使大脑形成了新的回路。基线扫描显示,电脑老手被激活的脑区在练习后被激活的水平与练习前相似。这表明,对于一个电脑老手而言,神经回路早期就已训练形成,并保持稳定。
背外侧前额叶皮质与负责决断以及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有关。通常认为这一脑区也控制着负责整合感觉、思维以及工作记忆的脑力活动。所谓工作记忆是指信息的短期记忆,如完成一项互联网搜索任务或者从电话簿获取号码后拨打电话等。
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智能电话随身携带,耳机时时挂在耳旁,笔记本电脑总是触手可及。Wi-Fi提供了随时联网的无线连接。
高科技革命使我们陷入了“持续性局部注意力”(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的泥淖之中。1998年,一家软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琳达·斯通(Linda Stone)创造了这个术语,用于描述那些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对什么事情都插上一脚,但实际上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用心的人。“持续性局部注意力”与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不同。后者指我们知晓每项任务的目的,并试图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如果只集中部分注意力,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时刻寻找机会与人进行某种形式的沟通。有消息来访我们才开始聊天,但我们时刻关注即时通信工具上在线好友的动态;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沟通占据了我们的边缘注意力(peripheral attention)。
尽管好友们不时上线似乎显得很亲密,但与关掉这些数字设备,在某一时期集中关注某一个人相比,我们正冒着与真实的社交关系脱节的风险,这种所谓的亲密感也并不真实。
科技大脑倦怠症
当持续集中部分注意力时,人们的大脑可能会处于高强度压力之下,无暇反省、沉思或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他们感觉自己仿佛身陷一场持续性危机——对新的联络、爆炸性新闻或消息时刻保持高度警觉。一旦人们习惯这种状态,便会对这种长久性连通(perpetual connectivity)乐此不疲:人们觉得自我和个人价值都从中得到了体现,并且对它无法抗拒。

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这一自我价值感可能有助于保护大脑中海马区的大小。海马区是内侧额叶处海马状的区域,负责新信息的学习和记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索尼娅·J·卢皮恩(Sonia J. Lupien)及其同事,研究了健康的年轻和年长自愿者海马区的大小。这项研究显示,人们的自尊程度与海马区的大小有着显著联系,这一点与年龄无关。他们还发现,人们越是感觉生活尽在掌控中,海马区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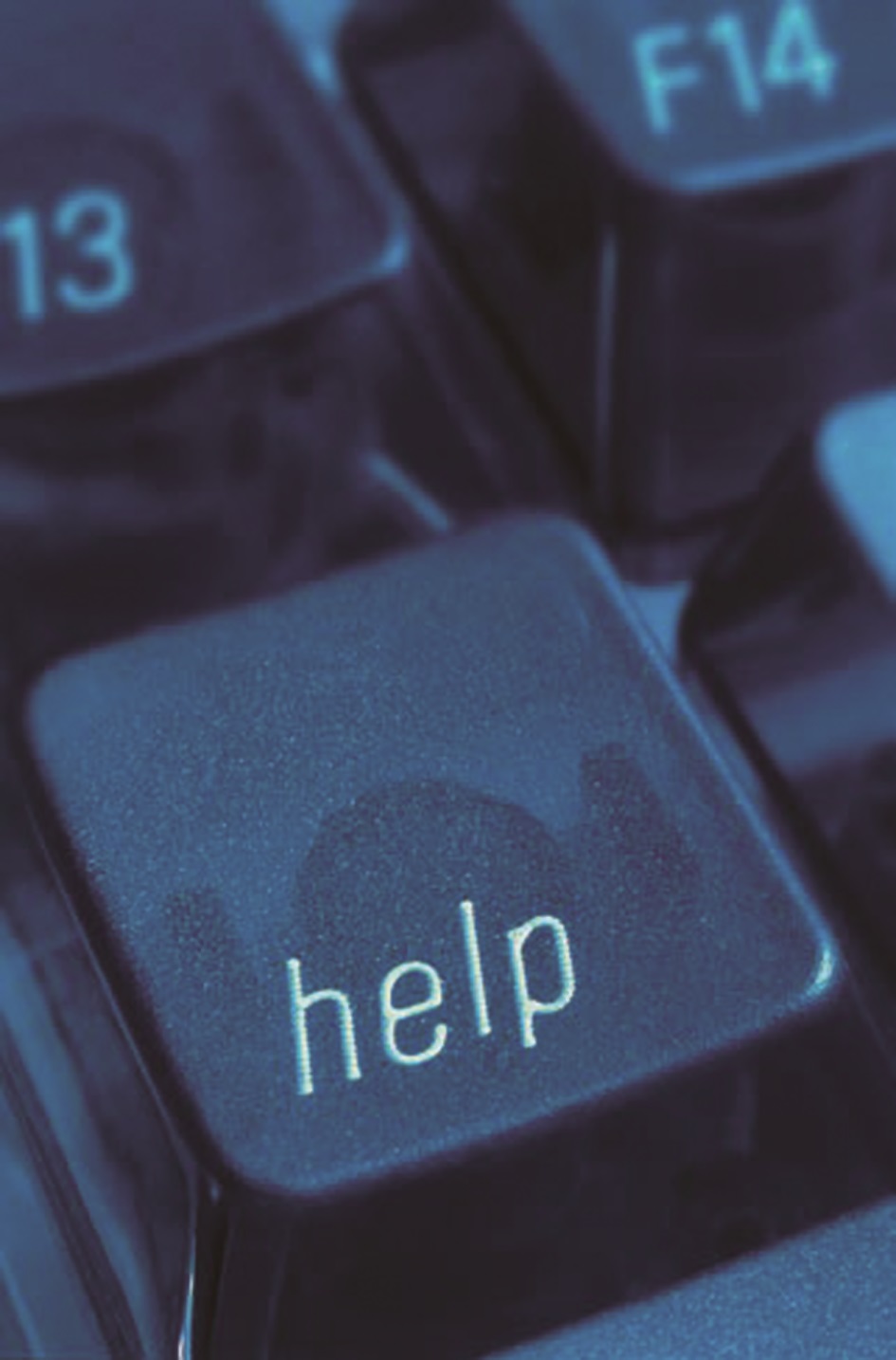
但有时候,当我们长时间保持局部注意力时,掌控感和自我价值感就会趋于崩溃——大脑无法在过长的时期内一直保持警觉。最终,数小时不间断的数字科技连通会导致一种特定类型的大脑紧张。许多人在互联网上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之后,就会频频犯错。停止工作以后,他们会感到精神恍惚、疲惫不堪、急躁易怒以及心烦意乱,就如同陷入了“数字化迷雾”中一般。这是一种新的精神压力,斯莫尔称之为“科技大脑倦怠症”(techno-brain burnout),它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病威胁人们的健康。在这种压力下,大脑会本能地发出信号,驱使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短期来看,这些压力激素会提升机体的能量水平并增强记忆,但时间一久,它们就会损害认知能力,从而导致抑郁,并改变大脑中海马区、杏仁核以及前额叶皮质的神经回路,而这些大脑区域负责控制情绪与思维。慢性、长期的科技大脑倦怠症甚至会改变大脑的基本结构。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专家萨拉·C·梅德尼克(Sara C. Mednick)与同事实验性地诱导自愿者患上温和科技大脑倦怠症,而后再通过小憩和各种精神调节方法减弱影响。受试者需要完成一项视觉任务:指出电脑屏幕左下角三条线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愿者的得分越来越低。但如果科学家使这些线条在电脑屏幕的左下角和右下角轮流出现,自愿者的表现就会有所改观。这一结果表明变更脑力任务的位置可以缓解大脑倦怠症。
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受试者能有20~30分钟的小憩,他们的表现会改善很多。很显然,与这项任务相关的神经网络通过休息又恢复了活力。然而,小憩时间达到60分钟,神经网络才会恢复到最佳状态。这段时间是人体到达快速眼动睡眠期所需的时间。
焕然一新的大脑?

不论我们是“数字土著”还是“数字移民”,电子邮件、视频游戏、谷歌搜索以及其他科技的使用,改变了我们的神经网络和突触连接。这些改变也强化了某些认知能力。我们能够学着对视觉刺激更快作出反应,并改善多种注意力,尤其是改进利用周边视觉(peripheral vision,是指注视一个固定物体的同时也观察到“超出眼角范围”的周边的人或事物)观察图像的能力。大脑的思维过滤器(mental filter)可以学会如何切换到高速工作状态,以使我们更好地筛选大量信息并判断它们重要与否。这样,我们就能够处理脑海中此起彼伏的大量数据信息。起初,面对海量信息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我们的注意力无法招架,但很快大脑就能够适应,并快速处理。
根据英国诺森比亚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帕姆·布里格斯(Pam Briggs)的研究,搜寻健康资讯的网络冲浪者在任何页面只须浏览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转换到下个站点。她发现如果受试者停留在某一站点,并对它有所关注,那么这一站点就包含与搜索相关的数据;而被受试者忽略的站点所含的数据基本都与目的信息无关。这一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学会了快速集中注意力、分析信息并即时决定是走是留的能力。这种情形与患上数字化注意力缺乏症(Digital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有所不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形成新的神经回路,以应对快速而直接的高度集中注意力的需要。

依据目前人们测量并定义智商的方法,数字进化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智能。随着数字文明的发展,平均智商指数在稳步上升,无差错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也得到了改善。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保罗·卡尼(Paul Kearney)报告称,一些电脑游戏确实可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多任务处理水平。他发现,自愿者如果每周玩8个小时的电脑游戏,多任务处理水平就会提高2.5倍。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玩视频游戏还会改善人们的周边视觉。随着大脑的不断进化,某些集中注意力的技巧还会不断提高,心理反应会更加敏锐,许多脑力任务的完成也会更高效。

如今,“数字土著”的大脑已与无所不在的网络搜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控制更传统的学习方式的神经回路却被忽视了,并在逐渐减少。由于人类惯常的一对一交流技巧在不断弱化,负责交往和沟通的神经回路也在日益萎缩。我们研究小组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研究显示,即使新近进化出来的、与科技相关的神经回路将大脑潜能推至一个令人惊讶的水平,我们仍然可以有意识地改变大脑回路,并使某些弱化了的神经回路再获新生。

无论是“数字土著”还是“数字移民”,都将掌握高新科技并利用它们的高效性能,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原本的交往技巧和人性。无论是与谷歌搜索有关,还是与移情式聆听练习(empathic listening exercise,是指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倾听)相关,神经突触反应都可以被测量并重新形成,向有益于我们的方向优化,我们的头脑也可以更加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