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起源》,提出人类起源于旧大陆(即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的一种古猿时,尽管遭到很多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却拉开了探索人类起源的序幕。
100多年来,古人类化石和基因分析结果都已证明达尔文是正确的。今天,一个普通学生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认识或许都胜过当年的达尔文。但即便最杰出的古人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种认识依旧模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不少结论尚缺乏直接证据,都是通过现有化石或基因分析结果推测得出,“想象的成分居多”。
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的陈淳教授也认为,“很多时候,一个新的发现不仅不能解开原有谜团,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疑问,使人类的起源变得越发扑朔迷离”。在过去100多年里,探索人类起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
起源于亚洲?

达尔文提出人类起源于猿类后不久,便得到了化石证据的支持。1892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瓦在印尼爪哇岛发现了一个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股骨,他认为这个古人类很可能就是人类的远祖,是人猿过渡的“达尔文缺环”。基于这个发现,当时大部分古人类学家都认为,亚洲是人类的起源地。
1924年夏天,南非威特沃斯兰大学的解剖学家达特在非洲一个名叫汤恩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幼年灵长类动物的头骨化石(后来被称作“汤恩幼儿”)。经过鉴定,他认为这块头骨的“主人”是一种与人类关系非常接近的古猿,很可能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因此人类的起源地应该是非洲而不是亚洲。可惜的是,达特的观点当时并未得到科学界的认可,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非洲是一片“黑暗”的大陆,过于落后和原始,不大可能是人类和文明的摇篮。
随后几年,中国和美国科学家的两项重大发现,让人们迅速遗忘了这个曾引起争议的“汤恩幼儿”。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的一个山洞内,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后来还在洞中找到了大量石器和和灰烬。经过年代测定,“北京人”大约生活在距今60万~20万年前(2009年3月,南京师范大学的沈冠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等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北京人”的生存年代应该在77万年前)。结合印尼爪哇岛和周口店的两次发现,科学家确立了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理论,认为最早的人类应该出现在60万~50万年前的亚洲。
1932年,美国古人类学家刘易斯的发现又一次震惊了世界。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发现了一件中新世晚期的灵长类动物化石——腊玛古猿(得名于印度梵文史诗《腊玛耶那》中的祭神首领)。由于化石上颌骨上的齿弓和牙齿与人类相似,因此刘易斯提出腊玛古猿可能是人科化石。虽然他的观点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也有很多科学家研究了腊玛古猿化石后,认为腊玛古猿是1400万~800万年前,与森林古猿分开而向人类进化的最早人类祖先。如果事实如此,人类出现的时间就将提前1000多万年,而亚洲作为人类起源地的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谁是最早的人类?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重大发现几乎推翻了此前关于人类起源的一切观点和理论。
1959年,英国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和玛丽·李基夫妇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找到了一个几乎完整的灵长类动物头骨化石,在化石不远处,还发现了石器和破碎的动物碎骨。李基夫妇认为,这种生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和屠宰动物,是人科的一种。为了感谢资助者查尔斯·鲍伊斯,李基夫妇把它们命名为鲍氏东非人。
后来几年,在“东非人”出土点附近,李基夫妇又发现了一些人科动物的头骨、下颌骨、肢骨等。这些动物的脑容量要比“东非人”大50%,李基夫妇将它们称为能人,并认为该地点出土的石器是能人制作的(于是鲍氏东非人被改名为南方古猿鲍氏种),它们才是人属最早的代表。经年代测定,这些能人大约生活在180万年前。李基夫妇的发现开始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怀疑,腊玛古猿可能并非人类始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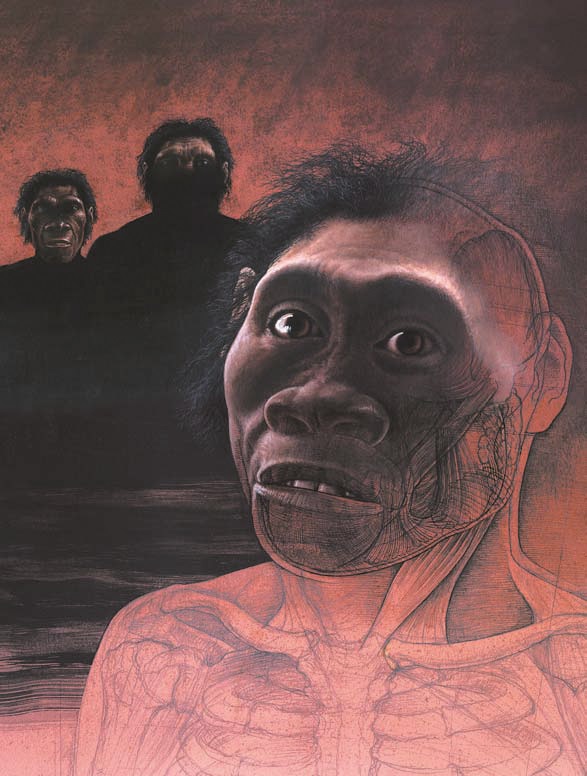
同一时期,科学界对“人”的判定也发生了重大转折。此前,科学家一般以制作工具为人类的标志,但英国动物学家珍·古道尔通过长期近距离观察发现,黑猩猩具有很多原本认为人类特有的行为特征(比如使用工具),因此古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两足行走才是人猿进化分离后最重要的变化,判定一种灵长类动物是否人类,应该以直立行走为标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相继发现十几具300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骨架化石(其中包括著名的“露西”)。古猿骨盆和膝关节上解剖学特征表明,它们已能完全直立行走,显然是“人”的一员,约翰逊把这些早期人类命名为“南方古猿阿法种”。由于在过去几年里,亚洲和其他大陆并未出土比“露西们”更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科学家把更多的目光瞄向非洲,而亚洲和腊玛古猿在人类起源上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
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基因分析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可以更精确地判定人和猿之间的关系——最终的分析结果表明,人与黑猩猩的亲缘关系最近,两者进化分离的时间大约在800万年~500万年前。这就意味着,腊玛古猿并非最早的人类成员,很可能只是某种古猿的祖先,因为它们的生存年代太过久远,而且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古猿可以直立行走。至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基本上为科学界接受,但也有少数科学家并不认同该观点,他们认为腊玛古猿的不少解剖学特征都与人类相似,而与类人猿不同,况且古人类学家从未找到800万年~500万年前人类化石。
化石证据并未让考古学家等待多久。1994年,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中部地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人类学家怀特发现了44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化石,并把它们命名为“地猿始祖种”。几个月后,怀特又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材料——至少5个个体的左颌骨、趾骨、肱骨、尺骨、锁骨和牙齿化石,存在年代距今约580万年。虽然化石材料上的不少特征与猿类相似,但也有与人科成员相同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从近端趾骨的解剖学特征来看,这些似猿似人的生物已能直立行走。怀特将它们命名为“地猿始祖种家族祖先种”,认为它们是与黑猩猩最接近的人类祖先。
不过,吴新智院士告诉记者,“最关键的两个发现出现在本世纪初”,正是这两个发现让绝大部分科学家相信人类起源于非洲。2000年,在肯尼亚图根山,一支由法国和肯尼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了12件化石,包括破碎的腿骨、臂骨和一些牙齿——这就是著名的“千禧人”,学名原初人图根种。年代测定表明,“千禧人”生活在620万~560万年前,比“地猿始祖种家族祖先种”还要早。研究小组认为,“千禧人”的牙齿相对较小,牙釉层较厚,这些特征都说明它们是人类的直系祖先。但这一结论也引起了争议。一些科学家认为,牙齿大小和釉层厚度与饮食习惯有关,并不能据此判定“千禧人”是人类祖先,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
2002年,当科学家还在争论“千禧人”是否人类祖先时,法国科学家米歇尔·布吕内在非洲西部的乍得境内,发现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一个头骨、一个下颌骨和一些牙齿化石,存在年代距今约700万年,被科学家命名为撒海尔人乍得种,可能是人科的最早成员。
由于头骨化石受到长期挤压而变形,反对者曾认为它们更像大猩猩的祖先。后来,研究人员对头骨标本进行修复,并用三维制图技术将化石逐一复原。结果表明,撒海尔人乍得种的解剖学特征与人类相似,而与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特征无法吻合。复原图还显示,这些古老人种是直立行走的,因为头骨眼眶上下缘直线与颅骨底面垂直,说明该动物呈直立姿势。面对确凿证据,“人类起源于700万~600万年前的非洲”终于为大部分古人类学家认可。
然而,对于谁是最早的人类,科学界仍不能完全肯定。吴新智院士表示,目前的证据只能说明在700万~600万年前,地球上已有人类存在,但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最早的人类,“或许未来某一天发现的证据,还会将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陈淳教授则指出了古人类学界的另一个困惑:地猿始祖种、原初人图根种和撒海尔人乍得种都曾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类,而且年代一个比一个早,但它们谁是真正的人类先祖,目前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也许今后新的发现会解开这个谜团”。
谁最早走出非洲?
古人类走出非洲,向其他大陆扩散,是人类进化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但与人类起源研究一样,要弄清楚这一里程碑发生的时间也不容易。
1959年,以色列科学家在约旦河谷附近的乌贝蒂亚,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具。经过仔细分析,科学家认为这处遗址是由早期直立人留下的,而古地磁法的测量结果表明,该处遗址的存在时间距今约100万年。
4年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等科学家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地带发现了一个直立人头骨化石,包括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当时的年代测定表明,“蓝田人”生活在80万~75万年前(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重新测定了“蓝田人”的生存年代,结果表明“蓝田人”生活在115万~110万年前)。而在欧洲,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海德堡人,生活在70万~50万年前,相关化石在1907年发现于德国海德堡东南约6千米处的一条河流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综合上述化石证据,古人类学家一般认为,以色列的乌贝蒂亚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因此最早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很可能是100万年前的直立人。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告诉记者,虽然发现“蓝田人”后不久,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钱方等科学家就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掘出“元谋人”化石和几件石器,但由于化石材料过少,仅有两枚上内侧门齿,“元谋人”的年代测定数据(170万年前)当时并不为科学界认可,因此“元谋人”化石也就没有对科学家的判断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发生在上世纪末的转折性事件,仍很快就让古人类家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可能有误。
德曼尼西是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西南方下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村庄,距第比利斯约85千米。在中世纪,这个村庄曾是一个著名城市,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因此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该地区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不过在此后多年里,该地区一直没有重要物品出土。
1983年,格鲁吉亚科学院的古生物学家阿贝萨龙·维库阿在一个储存粮食的地窖中,发现了一种早已灭绝的犀牛遗骸。这一发现让维库阿和同事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该地区可能还有更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化石材料。推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一年后,格鲁吉亚科学院的科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一批原始石器。
这些科学家决定加快发掘进度,以尽快找到人类化石,但上天和他们开了个玩笑——此后8年一无所获,直到1991年,他们才在一具剑齿虎遗骸的下面,找到了一块古人类下颚骨化石。他们认为,这块化石是直立人留下的,而根据同时出土的动物遗骸估计,这块化石的“主人”大概生活在160万年前。这样一来,“格鲁吉亚人”便取代以色列乌贝蒂亚遗址的直立人,成为非洲以外最古老的古人类。
1991年底,在德国召开的一次古人类学会议上,格鲁吉亚科学院的戴维和里奥向来自全世界的顶级古人类学家展示了“格鲁吉亚人”化石,他们的结论却遭到了质疑。与会科学家认为,这块下颚骨化石保存得太完好,连一颗牙齿都没有缺失,很难让人相信它有160万年的历史。很多人断言,这块化石并非直立人留下的,而来自一个比直立人更“年轻”的人种。由于没有得到古人类学界权威专家的认可,“格鲁吉亚人”渐渐被人遗忘。
但格鲁吉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并未放弃,他们继续在德曼尼西进行发掘。1999年,在距第一块下颚骨化石出土处几米远的一个地方,研究人员又发现了两块头盖骨化石。特征分析表明,这两块头盖骨化石与非洲直立人化石明显相似。同时,地质学家利用放射性断代法,测得化石出土处的火山岩沉积物的年龄为185万年。对化石所在土层进行的古地磁分析也显示,土层中的沉积物是在177万年前古地磁极发生反转时沉积下来的。
与这两块头盖骨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年代已经确定的动物遗骸,比如名为Minomys的啮齿类动物,它们生存在200万~160万年前。综合各种证据,科学家认为,“格鲁吉亚人”才是非洲以外最古老的古人类化石,而古人类首次走出非洲可能是在200万年前。
但“格鲁吉亚人”的身份却让科学家颇费一番周折。两个头盖骨化石的脑容量仅为770和650立方厘米,均低于直立人应有的脑容量。2003年7月,戴维和同事在德曼尼西又发掘出一个头盖骨化石,没想到这块头骨的脑容量更小,仅有600立方厘米,还不到现代人的一半。而且头盖上的一些特征也不像直立人——眉部纤细、面部向前凸出,后部弯曲弧度很大,这让科学家联想到直立人的祖先能人。
根据头盖骨以外的化石材料(比如肋骨、锁骨、脊骨、臂骨、脚骨等)来判断,“格鲁吉亚人”的体型稍大于能人,但又小于直立人。鉴于此,格鲁吉亚科学院的古人类学家认为,“格鲁吉亚人”很可能是能人与直立人之间的过渡人种或刚从能人进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但它们的确切分类,还需要更多化石证据的支持。
最近,弗洛勒斯人的特征分析也表明,最早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可能是比直立人更古老的能人(参见本期杂志《“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但吴新智院士向记者表示,由于弗洛勒斯人生存于1.8万年前,离现代时间太近,相关分析结果尚不足以作为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发现“蓝田人”的黄万波研究员曾于1985年,在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的龙骨坡,发掘出一段带有两颗臼齿的残破直立人左侧下颌骨化石,以及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片。后来的年代分析认为,这是200万年前的直立人留下的遗址。如果在200万年前,重庆市巫山县就有直立人存在,而由于中国与非洲相隔甚远,因此古人类肯定早于这个时间段走出非洲,前文关于古人类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论断就将受到挑战。可惜的是,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测定“巫山人”生存年代的方法有误,相关结果也不能作为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证据。
为什么走出非洲?
最早的人类在700万~600万年前进化出现,为什么直到200万年前才首次走出非洲?一些科学家认为,早期人类必须要进化出较大的脑容量,学会制作比较复杂的工具后,才可能走出非洲,因为只有这样,前往其他大陆后,才能比较轻松地寻找和猎取动物。
吴新智院士就表示,古人类走出非洲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寻找食物。200多万年前,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多,非洲大陆上可供捕杀的猎物相对减少,于是一些古人类就开始四处迁移,寻找新的食物源。它们的迁移方向并不固定,恰好有一批古人类幸运地向北迁移,从亚非大陆相连接的地方走出非洲,进入亚洲,演出了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一幕。根据世界各地已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科学家大致推测出了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路线:从非洲中部出发,经过中东到达格鲁吉亚,再由格鲁吉亚,分别向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迁移。
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次数,也是科学界的争议焦点。现在广为人知的“迁移事件”主要有两次:一次是200万年前古人类首次走出非洲,另一次就是15万~8万年前,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参见《环球科学》2008年第8期《现代人身世之谜:DNA记录人类迁徙路线》)。但在200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他和同事利用自己在1995年设计的一套计算机程序,重点分析了10个区域(根据遗传特征划分)的人的普通染色体、性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结果发现古人类曾在84万~42万年前和15万~8万年前两次走出非洲。
2005年,坦普莱顿将分析区域扩大到25个,结果显示,除了上述两次外,古人类还于190万年前从非洲向其他大陆迁移,因此在人类进化史上,古人类总共三次走出非洲。他把相关分析结果发表在《2005年体制人类学年鉴》上。
这篇文章受到古人类学家的强烈质疑。吴新智院士表示,很多古人类学家都认为,早期人类很可能是多次走出非洲,而且“不仅有走出,还有走进”,因为古人类的迁移是随机的,并不会始终朝某个方向迁移。他还认为,坦普莱顿的观点站不住脚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在整个人类进化史上,早期人类只曾三次走出非洲,这说明在某些时段,肯定是气候变化或地质条件阻止了古人类向外迁移,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关证据表明,在过去200万年里发生过这样气候变化,或存在不利于古人类走出非洲的地质条件。
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很多谜团似乎都有了答案,但是否最终答案,仍需更多化石证据的支持。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