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细菌追踪罪犯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能够推断微生物间亲缘关系的新技术,
已经在民事与刑事调查领域初显身手,但要将其作为呈堂证供,还需慎之又慎。
撰文 沙奥尼·巴塔查里亚(Shaoni Bhattacharya) 翻译 朱机
麻醉师胡安·马埃索(Juan Maeso)住在西班牙海滨城市巴伦西亚,在外人看来,他过着颇为体面的生活。可实际上,马埃索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在两家医院工作过,在至少10年时间里,曾多次在给病人使用吗啡前先自己揩油,随后就拿自己用过的针头继续给病人注射。
2007年马埃索罪行败露,他因造成至少275名病人感染丙型肝炎,且其中4人死于并发症,而被判处1 933年监禁(但根据西班牙法律,他只需服刑20年)。
马埃索始终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一口咬定病人是自己感染的丙肝病毒(HCV)。但就在去年,巴伦西亚大学的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坎德拉斯(Fernando González-Candelas)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作为证据,认为其中的事实与马埃索的申诉完全相反。他们采用了一种名为“种系发生学鉴定”(Phylogenetic Forensics)的手段,对近4 200份病毒序列进行了分析和归类,推测患者感染HCV病毒的历程和先后顺序。
这种技术结合了进化生物学的手段和现代测序技术,目前已经逐渐在犯罪调查、民事调查和生化防范领域推广应用。比如,2014年2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就介绍了如何利用这项技术,追踪一批携带炭疽病毒的海洛因的来源——自2009年以来,这批毒品已经造成欧洲各地多名吸毒者的死亡。
但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进化遗传学家安妮-米克·旺达姆(Anne-Mieke Vandamme)认为,这项新技术要在司法领域中应用,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2002年以来,她参加了19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其中大多是为辩方提供服务。目前,DNA鉴定已被全球大部分司法系统认可,但“种系发生学鉴定”就未必有那么可靠了。“你永远都无法用这些证据证明某人有罪,”她评价道。
除上述问题外,还有社会舆论方面的顾虑。很多患者权益组织认为,追查感染途径的做法,可能会让艾滋病等疾病的患者处境更为尴尬。随着测序技术和分析工具的不断进步,在司法领域中采用“种系发生学鉴定”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目前,旺达姆和她的专家团队正在制定一部指南,以期能从技术和流程两方面给出明确地指导意见,推动新技术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她希望“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能对这项技术的能力与局限有明确的了解”。
巴伦西亚案
马埃索的罪行之所以会败露,是因为西班牙公共事业公司的医生留意到工人群体中出现了HCV集中感染的情况。在查阅这些工人的病例时,一位名叫曼努埃尔·贝尔特兰(Manuel Beltran)的医生注意到,这些患者都曾于数月前在一家名为“健康之家”(Casa de Salud)的医院做过小手术。
于是,贝尔特兰与当地公共卫生机构取得联系,最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行动,对两家医院超过66 000份病例进行了彻查,并很快发现,其中很多病例都指向马埃索。不过,检察官还需要更多证据。
“种系发生学鉴定”就是在这时登场的。HCV、HIV和流感这类病毒的突变速度非常快。通过对从不同个体中提取的病毒样本进行测序,并比对它们基因组中的微小差别,科学家可以追溯它们的演化过程,并绘制病毒的进化树。英国牛津大学的进化问题和传染病专家奥利弗·派伯斯(Oliver Pybus)说,“其实,我们就是给病毒编制一个家谱”。
这个过程可以帮助科学家推测两次或多次感染过程之间的关联性有多大,以及具有什么样的关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类信息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一些蓄意感染案的调查中,已经应用了这项技术。例如1998年,理查德·施密特(Richard Schmidt)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法院判处了二级谋杀未遂罪:此人给前女友注射了被HIV和HCV污染的血液,却谎称打的是一针维生素B12。这项技术还曾用于著名的炭疽邮件案,本案涉及美国多家媒体和多名政客。2001年,美国发生了犯罪分子向警察局和新闻机构投递炭疽孢子邮件的案件,当时也采用了“种系发生学鉴定”技术来调查炭疽杆菌的来源。而在涉及疾病传播的强奸案和儿童性侵犯案的调查中,也会利用该技术来提供相关证据。
不过,“种系发生学鉴定”与更为与陪审团熟知的DNA鉴定有很大的不同,旺达姆介绍说,DNA鉴定能够确凿地证明某人是否有罪,而“种系发生学鉴定”只能提供附属证据,即证明A体内的病毒很有可能来自B,但无法100%确定A体内的病毒来一定来自于B。
HCV具有高度的变异性,坎德拉斯和同事根据其基因组内高度可变区(highly variable region)的变化情况,把不同的病毒样本排列在树状结构的不同分支上,以标示它们的演化关系。科学家分析了321名受害者携带的病毒样本,认为平均每人体内有11条病毒序列来自马埃索,而同时进行测试的另外42名对照患者(即当地的其他HCV感染者)则与本案无关。研究人员为本案绘制了进化树,打印出来足有11米长。
利用这些数据,研究团队为每个感染者计算出一个“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即“直接或间接通过马埃索感染HCV的可能性,与感染其他病源的可能性的比例”。由于感染者样本数量很大,而且彼此间具有明显的种系发生相关性,所以得出的似然比数值也非常高,绝大多数超过105,最高的达6.6×1095,这也说明了这种分析结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对巴伦西亚案件的研究过程中,还运用了“分子钟”(molecular clock)技术,对感染者接触病毒的时间进行了精确推测。为此,研究人员对每位感染者体内HCV病毒的遗传差异进行了取样分析,然后根据症状发作时HCV病毒的突变率来估算感染的具体时间。其中近2/3的估测日期与患者去医院就诊的日期相符。这样,马埃索是感染源的证据就得到进一步加强。
不过,要在法庭上呈现这些数据却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为此坎德拉斯和同事莫亚(Andrés Moya)不得不专门花了两天时间给法官和律师上课,帮助他们熟悉相关的专业名词和概念,之后才开始了为期三周的专家证词陈述。
科学家必须让法官和律师明白,这种方法与DNA鉴定是不一样的。法官要了解这种分析方法的内在复杂性:因为HCV突变速度非常快,患者感染时间越久,携带的病毒就越具有多样性。
如果这名患者再感染其他人,那么他体内携带的任何一种变异病毒都可能传递给别人。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病毒样本进行分析,但这样就有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关联,也有可能得到错误的关联结论。“相关个体之间,甚至单个个体内的病毒样本都不可能完全匹配。”旺达姆说。即使案例中两个或更多个体中的病毒确有相关性,也会得出好几种不同的进化树,这完全取决于采样时间和感染过程中有多少种病毒变异体被传播。
在本案中,“种系发生学鉴定”证明了马埃索与大多数患者的关联。但同时,也帮他排除了与47名感染者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因此,这些人未被纳入补偿名单。坎德拉斯说,“我们的分析是公正客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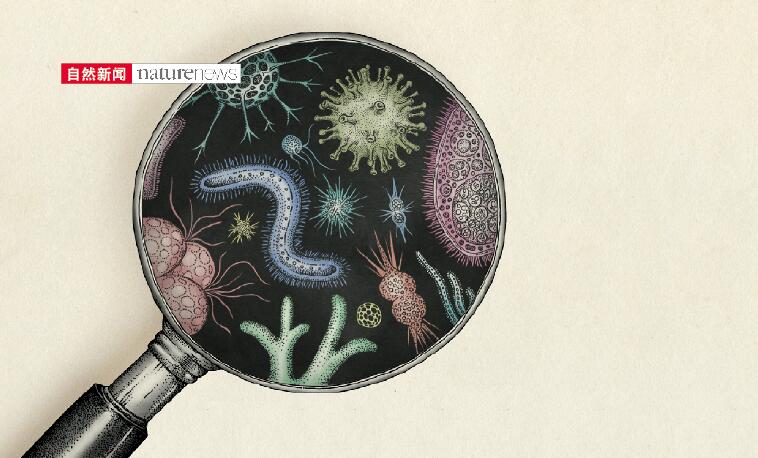
司法上的障碍
许多科学家认为,新技术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帮助嫌疑人洗清罪名。2004年5月,5名保加利亚护士和1名巴勒斯坦医生在利比亚被判处死刑,原因是涉嫌在班加西的阿尔-法塔赫医院(al-Fateh Hospital),故意给426名儿童注射HIV病毒。
而根据“种系发生学鉴定”的分析结果显示,涉案的HIV病毒在“班加西六人”来到利比亚之前数年就已在当地传播了。2006年,就在对这六人的重审即将开始之前,《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这一结论,然而法庭还是维持了死刑的原判。研究团队成员派伯斯介绍说,虽然研究成果没能改变判决,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交关系。2007年,“班加西六人”获得减刑,被改判为终身监禁,随后被引渡回保加利亚,并最终获得保加利亚总统的赦免。
这几个案件成为“种系发生学鉴定”发展的转折点。2010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戴维·希利斯(David Hillis)及其同事报道了一种方法,可以在病毒传播的走向上,首次给出支持性证据。
希利斯说,研究人员需要仔细检查感染者携带的病毒种群。因为每个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都存在多种变异体,其中一部分变异体会传染给其他人,之后又会在新的感染者体内迅速繁殖并发生变异。因此,很有可能会出现传染源与感染者体内携带病毒的亲缘关系较近,甚至超过同一个人体内病毒间亲缘关系的情况。理清病毒变异体间的亲缘关系,将有助于识别出谁是传染源,谁又是感染者。
最新测序技术的出现,也有力的推动了“种系发生学鉴定”的应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安德鲁·兰博(Andrew Rambaut)也和派伯斯一起,参与了“班加西六人”案件的调查工作,他说,“提取的样本越多,获得的结果就越好,也越完整”。
布鲁斯·布道尔(Bruce Budowle)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研究院工作了26年,他认为,快速自动测序技术能够为研究人员提供海量信息。目前,布道尔在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担任应用遗传学研究所主任。
但信息量太大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布道尔说,必须采用满足司法要求的方法对庞杂数据进行处理,才能将这些数据用于司法用途。如果相关的软件或方法没有通过司法认证,所得到的结论就会遭受法庭的质疑。
布道尔和他的同事在2001年的炭疽邮件案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为了描绘炭疽杆菌的进化树,他们不得不采用了由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微生物学家保罗· 凯姆(Paul Keim)开发的一种技术,但这种技术并没有经过司法认证。布道尔说:“这种方法让我们对整件事情有了头绪,并且发现案件中的炭疽杆菌的菌株并非来源于自然界,而是来自一家实验室。”
这个线索帮助调查人员追查到炭疽杆菌的来源:艾姆斯菌株,随后又发现了这一菌株的变异体与布鲁斯·艾文斯(Bruce Ivins)的关联——艾文斯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微生物学家。但在2008年,艾文斯受到FBI调查后就自杀了,所以此案无法开庭,也就没有人能说清,在本案中通过“种系发生学鉴定”获取的数据究竟有多重要了。
采用“种系发生学鉴定”技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给感染者带来名誉上的问题,尤其在与HIV感染者或与传播HIV相关的案件中,对此更加敏感。在某些国家,那些无意中、或在未告知对方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播给性伴侣的人,会被以杀人、杀人未遂或人身伤害的罪名指控——即使受害者最终并没有感染HIV。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由于对“种系发生学鉴定”的顾虑,会影响人们进行病毒检查的积极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种系发生学鉴定”领域中部分科学家不愿再参与案件的调查工作,要不就是非常谨慎地挑选某些特定案件出手。安德鲁·利·布朗(Andrew Leigh Brown)在爱丁堡大学研究HIV病毒的进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协助司法调查,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再接手类似案件了。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于2013年5月发布了一份政策性文件,布朗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份文件号召停止对非蓄意HIV传播事件的起诉。其目的十分明显,对“种系发生学鉴定”的应用必需慎之又慎,同时还需要有其他附属证据的支持,文件建议:必须要加重举证的责任。
潜在用途与隐患
令旺达姆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对于“种系发生学鉴定”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目前还缺少规范性指导。旺达姆正与其他专家共同起草一份指南,她希望这样可以帮助科学家少走一些弯路。除了完善新技术在司法领域应用的流程外,她还设想能在技术层面上达成某些共识,比如怎样选定对照人群,应该评估病毒基因的哪些特定区域等。“这将有助于‘种系发生学鉴定’更好地服务于司法领域”。
科学家们表示,对于参与案件调查,他们还是会采取慎重态度。“尽管我们能够检测病毒的亲缘关系,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最符合社会利益的做法。”
尽管巴伦西亚案已过去数年,但相关研究数据的公布却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种系发生学鉴定”潜在用途和隐患的讨论,这不仅涉及法律程序,还涉及生化武器防御的有关问题。在2013年10月于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进行的一次会议上,坎德拉斯在报告中介绍了这一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
这次工作会议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英国皇家学会(UK Royal Society)等机构共同主办的,目前会议相关论文还没有发表。但据布道尔说,当下对于数据获取和使用的权限问题存在很大争议,出于风险考虑,从事生物安全和来自情报界的与会者希望对数据进行保密处理。
布道尔表示,在这种人命关天的问题上,必须要作出正确的决定。“种系发生学鉴定”的结论将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甚至会使一个群体受到社会的歧视。在涉及生物武器的事件中,一个结论或许就会引发制裁,甚至战争。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确保检测手段的准确性万无一失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布达沃说,“技术手段的发展也必定会日新月异。”
本文作者 沙奥尼·巴塔查里亚是一名自由科学撰稿人,居住在英国伦敦。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