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预言者
通过测量端粒的长度,可以迅速预测你患心脏病、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的几率,衡量出你当前的综合健康状况和衰老情况——这种技术的推动者,就是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伊丽莎白·H·布莱克本。
采访 西娅·辛格 (Thea Singer) 翻译 赵瑾
虽然伊丽莎白·H·布莱克本(Elizabeth H. Blackburn)对于端粒工作机理的开创性研究是在几十年前,但“分子计时器”这一存在于每个细胞内的物质,其名称却又一次出现在新闻头条。最近,布莱克本与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显示,这些被称为端粒(telomere)的“细胞时钟”,很可能成为人体健康的晴雨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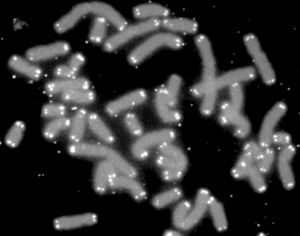
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DNA片段,它能够避免染色体之间的相互磨损、黏着,起到保护染色体的作用。然而,细胞(如免疫细胞和皮肤细胞)的每次分裂,都会使端粒变短。这个特性使端粒长度成为衡量细胞衰老的指标之一。在一些细胞中,一种叫做端粒酶(telomerase)的蛋白质能够重新合成端粒缺失的部分;而在另一些细胞中,端粒则会持续缩短。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时,细胞不是死亡,就是停止分裂,进入休眠状态。2009年,布莱克本与她的研究生、现任职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卡罗·W·格雷德(Carol W. Geider)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杰克·W·绍斯塔克(Jack W. Szostak),凭着他们在端粒机理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目前,任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布莱克本仍没有打算停下脚步。2004年,她与健康心理学家伊莉莎·S·埃佩尔(Elissa S. Epel)发表了一篇论文,将心理压力同白细胞中的端粒缩短联系起来。现在,已有多项研究显示端粒的缩短与多种疾病有关。相反,经常锻炼,或者释放压力,端粒似乎会长一些。这些研究都表明,通过简单的血液检查,就可以测定端粒的长度,从而进一步衡量人体的综合健康状况和衰老情况。
去年,布莱克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门洛帕克市与其合伙人创立了一家名为“端粒健康”(Telome Health)的公司,希望通过医疗服务机构为研究中心及个人提供血液细胞的端粒检测服务。在西班牙马德里市,一家名为“生命长度”(Life Length)的公司也开始向公众提供端粒检测服务。这些消息一见报就引起了公众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这种检测到底有没有用。最近,科学作家西娅·辛格就布莱克本的相关研究,对她进行了采访。
《科学美国人》:我们听过许多关于端粒变短会影响细胞衰老的研究,但端粒缩短究竟怎样影响人体的衰老呢?
布莱克本:多项研究显示,通过对端粒长短的检测,不仅可以预测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甚至能够预测个体死亡的风险。玛丽·沃莱(Mary Whooley)是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同事,她在“心灵及精神研究”项目(Heart and Soul Study)中,对780名60岁及以上的老人进行了4年的跟踪调查。结果证实,端粒的缩短确实是影响死亡率的一个风险因子。美国犹他大学的遗传学家理查德·考森(Richard Cawthon)对143名研究对象进行了一项长达15~20年的研究,也发现端粒较短个体的死亡率是端粒较长个体的两倍。
《科学美国人》:如此看来,我们或许应该改变我们谈论端粒缩短的方式,并且将“衰老”和“细胞衰老”这些词换成“患老年疾病的风险”。
布莱克本:是的,我认为的确是这样。我并不是很喜欢“衰老”这个概念,因为我认为它并不包含实质性的、有用的信息。
《科学美国人》:目前,有哪些证据显示长期压力和童年心理创伤与端粒变短有关?
布莱克本:让我们先来谈谈童年心理创伤吧。多项研究发现,童年心理创伤的次数与成年后端粒缩短的程度呈量性相关,即心理创伤次数越多,端粒就越短。我们的研究还显示,慢性疾病患儿的母亲在照顾患儿期间,承受着长期的精神压力,照料时期的长短与母亲体内细胞端粒缩短的程度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科学美国人》:长期研究还显示,我们可能减缓端粒缩短的速度,或者甚至通过改变行为方式(例如饮食和锻炼)来增加端粒的长度。请谈谈这方面的进展吧。
布莱克本:我们曾对患有冠状动脉疾病且病情稳定的病人进行为期5年多的跟踪观察。结果发现,血液中Ω-3脂肪酸水平较高的人,端粒缩短程度总体较低;而那些在5年中端粒变长的个体,大多数人血液中的Ω-3脂肪酸在研究一开始水平就较高。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此项研究的数据收集,只是还没有发表。
《科学美国人》:我们是否应该提高Ω-3的摄取量?
布莱克本:参加此项研究的病人现在都已是60多岁的老人,并患有轻度的冠状动脉疾病(在研究开始时,病情都比较稳定)。所以,提高Ω-3的摄取量只对这一人群适用,可能并不适用于八九十岁的老人,以及15~20岁的年轻人。
《科学美国人》:你曾说过,以前的医疗模式都是通过检测确定病因,然后选择一种治疗方法来消灭某一种病原体。但现在,医生遇到的慢性疾病常常不是单因素的疾病,那对于这种情况,端粒研究能给医生提供哪些帮助?
布莱克本:端粒研究一般不会针对单一疾病的诊断。我们所要观察的是,那些常常扎堆出现、常见于老年人的进行性疾病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我们认为,这些疾病可能具有相似的发病机理。现在,有一种让人很感兴趣的说法:慢性炎症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共同致病机制,比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只不过目前我们还在分别看待和治疗这些疾病;而通过检测白细胞中端粒的缩短程度,我们可以发现和诊断慢性炎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炎症就是由端粒缩短导致的。所以,端粒长度这个指标其实反映了多个层面的生理问题。
《科学美国人》:你认为临床医生知道这些说法吗?
布莱克本:我认为临床医生或许还在衡量这种检测的可行性。但我认为,把端粒长度作为一个监测指标是值得尝试的。
《科学美国人》:你曾在一篇关于“截杀癌症”的论文中提到,在癌症发作之前,就使用药物或其他方法将它扼杀在萌芽阶段。这与上面提到的想法不谋而合。
布莱克本:是的。“截杀癌症”的重点在于及早阻断,也就是在你的疾病完全成形之前,就开始对它们进行干预,以避免更大的人力和经济损失。通过癌症研究,我们对癌症发生阶段的认识越来越提前,对癌症发展过程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因此,我们现在知道,某些抗癌药可能是在特定癌症发生的极早期发挥作用。如果再将这个想法推向极致,那就变成,我们可以检测哪些因素可能致使哪些人患上哪种癌症,然后在其发病之前就给予相应的治疗。目前,科学家已针对一组结肠癌高危人群展开研究,并找到了一些方法来阻止结肠癌的发生。
《科学美国人》:在这场癌症狙击战中,端粒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布莱克本: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端粒缩短在小鼠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癌症风险因子。虽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它对人体的影响,但在部分人群中,端粒缩短的确可以预测个体患某些癌症的风险。一种可能是,端粒缩短由免疫功能衰退引起,当检测白细胞中的端粒时,其实是在对免疫系统进行检查。另一种可能是人体内存在慢性炎症,因为它也能导致癌症。又或者,癌细胞本身端粒过短,致使基因组不稳定,最终引发癌症。
《科学美国人》:端粒长度和患癌风险是否和遗传有关?
布莱克本:很有可能。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顾健(Jian Gu)曾做过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他和同事希望通过客观分析,来确定端粒缩短与癌症风险在遗传上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他们的研究主要针对膀胱癌,想弄清楚基因组上的哪些变化与癌症风险有关。结果发现,一种基因突变与端粒缩短和癌症风险都有关系。随后,他们又对这个基因本身进行了研究,结果又让他们吃了一惊:该基因还与免疫细胞的功能有关。
《科学美国人》:最近有新闻称,端粒检测可以预测寿命。请你解释一下,就目前的科学水平,端粒检测到底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信息?
布莱克本:这些都是很愚蠢的说法。端粒检测并不能诊断疾病,它也没法告诉你,你是否能活到100岁。但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告诉你一个概率——随着年龄增大,你有多大可能患上某种疾病。除了我们公司,还有一家公司也在提供端粒长度检测服务,它的名字叫做“生命长度”。我想,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个名字可能具有某些暗示意义,它不是一个好名字。
《科学美国人》:哪种端粒检测方式最有效?
布莱克本:我们还不清楚哪种方式最好,但我们知道,你可以用6个月,甚至4个月的时间观察端粒长度的变化情况,但绝不能只用一周时间。根据科学原则,你绘制的曲线包含的测量点越多,就越能准确推测变化趋势。因此,6个月的测定方式可能更合理些。
《科学美国人》:听起来,端粒检测类似于胆固醇检测:首先会有一个针对与你同龄、同性别,而且生活方式也与你雷同的人群的标准,然后把你的情况与该标准进行对比,进而得出一个百分比。
布莱克本:是的。不过,胆固醇明显是与心血管疾病相关,而端粒检测却没有这么强的针对性。你可以把这种检测跟称体重归为一类,因为端粒和体重一样,都是反映多个健康层面的指标。显然,超重肯定不是好事,同样,端粒太短也不好。不过,体重会有一个健康范围,医生会把这个范围作为指标,然后跟踪监测病人体重的变化情况。我想端粒长度也与此类似,也是一个可以反映多种因素的指标,而且在临床中,你不会单独使用这个指标。
《科学美国人》:批评端粒检测的人曾说,检测胆固醇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数据,可以让科学家建立胆固醇的高低标准,然而对于端粒长度,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数据来界定正常范围。
布莱克本:我不这样认为。如今,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我们不会把所有人都归为一类,而是分为不同的组群。在不同的组群间,端粒的长度各不相同,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这方面的数据。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基本明确了端粒长度的大致范围。
当然,知道得越多越好,但你总得有个开始吧。而且,对于端粒检测的需求不只局限于研究机构,个人对它的需求也十分强烈。我们只是想先将这些检测推出市场,但并不会夸大其准确性。
《科学美国人》:你为什么决定开办公司,而不是继续在实验室开展端粒检测?
布莱克本:对于这类检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可靠的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我们实在没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只好由公司来开发这项技术。
《科学美国人》:人寿及医疗保险公司可能以端粒检测的结果作为参考,决定投保人的受保范围。人们对此忧心忡忡,你有何看法?
布莱克本:我们不能隐瞒信息。但是,我们会确保我们所提供的所有临床信息是准确的,只在恰当的情况下披露,不让保险公司滥用其作为拒保的理由。另外,由于端粒检测只能提供某种概率,如果保险行业将它们作为承保与否的依据,很难站得住脚。不过,对于个人来讲,我们不应对端粒检测的结果掉以轻心。我们提供端粒检测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健康。
《科学美国人》:有些批评者常把端粒检测与那些炒得很热的基因检测放在一起比较。基因检测通常采用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营销模式,帮顾客找出基因变异,分析其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那么端粒检测与此有何不同?
布莱克本:端粒检测不会采用这种营销模式,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会从今年10月起,通过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为公众提供端粒检测。
通过对多个组群的多项研究,我们已经在端粒缩短与疾病风险之间建立起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联系。近年来,端粒研究发展迅速,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有时已跟不上它的发展。
《科学美国人》:你会不会检测你自己的端粒?
布莱克本:那是一定的,一旦公司开始为个人提供端粒检测,我就会去检测自己的端粒长度。我对此很是期待呢。
本文作者 西娅·辛格是美国波士顿的科学作家。
本文译者 赵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
请 登录 发表评论